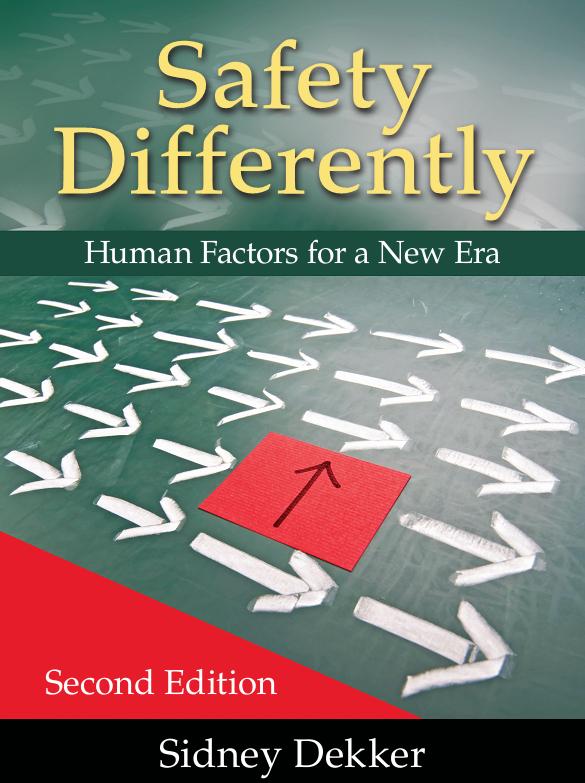“人”是需要控制的一个麻烦,还是解决安全问题的途径?有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安全管理都被这样一种思想所统治:“人”是被管控的目标。“人为因素(human factor)”是研究有关人类个体的以及人类“精神、身体、道德品行“的科学。“人”的确是需要控制的一个麻烦。我们要小心地选择合适的“人”,不单单是考量此人的能力多强,而是考量这个人是否有缺陷或瑕疵。然后,把这个人塑造成能满足固定技术特点以及工作环境要求的人。解决安全问题是通过控制工作中的人来解决的。
20世纪中叶,这种思想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随着技术越来越复杂和科技变化的脚步越来越快,并伴随着对基本科学规律怀疑论的兴起以及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rist psychology)的实际作用,构建并带动了安全思想的很多基础意识形态的变化。新的“人为因素”就是在这一变化中萌芽的。它证明了人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无论个体差异如何,技术应该被用来适应每个人的强项和弱项。解决安全问题更多地是通过控制技术、环境和系统来解决的。
最近的40年里,我们已经认识到,重大的灾难(如:炼油厂爆炸,航空事故)都和相关的组织机构的工作(或者不工作)脱不了关系。错误的开头并不是由“人”造成的。“人”只是收到了错误,并且“继承”了错误。建设并运行航空公司、燃气管道、医疗系统、航天飞机或客运船只的过程中会造就大量的组织机构网络,以便支撑整个系统的运转,并且推动、发展、控制和规范自身产业。当技术变得更复杂时,就离不开它的组织和机构。承运人、监管者、政府部门、制造商、分包人、维修机构、训练机构,所有的这些从道理上说都是用来保护和保证技术运转的。他们的各种限制,归纳起来就是阻止事故的发生。自从1978年的三里岛核电站(Three Mile Island)事故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原先被认为对技术安全和稳定运转非常有效的组织(操作员、监管者,管理者,维护者),事实上成了事故的主要推手之一。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就不可能出现错误。
这种认识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推广和接受了。与其控制组织内的单个人为因素,不如把安全资源用于整个系统,用于整个组织,用于各种设计问题,用于造成问题或安全风险的运行和组织束缚,用于所有人。但是这种认识也有自己变化、反复、转化的种子。有人逐渐认为安全管理就是管理者的命令和管理的控制过程。在20世纪晚期,最流行的系统安全模型就是瑞士奶酪模型(Swiss Cheese Model)。这个模型认为,一个错误是由组织和管理层上许多前期的小错误发展而来的。由于它再次强调了,错误是因为系统内很多人造成的,而非只有一线的人,所以这一模型理论同样被加强并传播甚广。但是这个模型的问题是,它把风险具体化成了“牛顿化”的思维,风险就像储存着的能量,而且模型表述的因果关系是线性的。这种“牛顿化”的思维模式事实上阻碍了我们发展最初的“人为因素”新思维,这种原本的、不同以往的新思维可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纷乱世界。而且,这种新思维并没有否认历史上“人需要控制”的论断。如果组织架构上的保护是有缺陷或瑕疵的,那么不但会造成糟糕的流程、不合适的设计,而且还会(用模型的话来说)造成违章操作、危险的行为、一连串的管理缺失、决策失误、缺乏监管。
最重要的是,新思维描绘了一副现代思维的场景:一线工作的安全运行,是由上游系统(upstream system)的良好管理和先进技术来达到的。我们需要在上游系统中查找错误和填补漏洞,来避免一线的错误。我们要对官僚机构和管理者有信心。此外,也要对科技和技术有信心。这样做是正确的事,也是目前应该做的事。虽然,这样做加深了主要通过“计划、处理、书面工作、审计和监督检查”来达成安全的原有想法。这样做也造成了在安全管理系统中过度注重查摆(count and tabulate)在按章操作检查、监控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negative events)”。因此,这样做也造成一线员工的新限制增多。这种解放的态度(emancipation),是伴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人的思想变化造成的,又被“人为因素”的新思维实体化了。不过,这种解放的态度招致了一种“反革新(counter-reformation)”。那就是,安全更多的时候意味着屈服于对责任的顾虑,对协议、保险重商主义(insurance mercantilism)的崇拜,对法规和诉讼的恐惧。在许多行业中,安全从运行的结果,渐渐变成一种管理手段。安全从“对于从事危险工作的员工的道德责任”,变成了“那些想要控制整体风险的人的是否对官僚机构尽责(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所以,安全机构应运而生。安全机构越发展,离运行第一线越远,还往往被“防火墙”和负面指标围绕着。安全机构总是想罗列出一张“损失”、“控制”和“限制”的词汇表。“人”再一次地变成了被控制的目标。臃肿的安全机构会使得上层组织倾听技术建议和获得运行经验的机会慢慢变少,中层领导和监管层的力量会减弱。员工会再也感觉不到被鼓励或者有可能审视自己的不足。安全机构还扼杀了创造能力,限制了员工的主动性,转移了问题的本质(erode problem ownership)。
===========================
我个人觉得最后一段说的非常对,我深有体会。